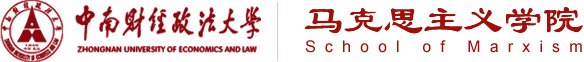导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已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也有些人开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们以西方为普世,以美国为绝对标准,似乎中国改革若不合美国的标准,就统统都不达标。这样的结果只能使中国的改革走向它的反面。中国自己的路不是由所谓的“普世”标准决定的。我们看待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自己的路不是由所谓的“普世”标准决定的。我们看待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有“左”的教条主义,如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文革”中的“左”倾严重错误;也有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实践,因为人民群众不能接受脱离实际的政策并一定要对其抵制。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他们对中国国情的感受是最深的。政策正确与否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判定的。目前西方推广他们的“普世”标准,是有特定目的的,这就是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体制要以西方为绝对样板。从目前一些国家比如苏联、利比亚、乌克兰等国的实践看,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中国目前有人提出的所谓“宪政”,就是以西方的“普世”尺寸裁量中国,其目的就是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一切政治体制如不符合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标准,他们就说你还不够“普世”。这对中国是要命的事。
“久病成良医,良医治久病”,这句老话讲的既是实践的道理,又是认识的道理。得过慢性病的人知道,治病方子不能一成不变,而要因时因地因人调整。我们当然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生活做他们的试验田。前几天有个同志从美国回来,带着美国的观念,他不看美国的国情也不看中国的状况,天然地就说中国不行,并以“昆明事件”为例。我说,“昆明事件”在中国是个大事。那在美国算不算大事?在美国横扫十几人的枪击案已见怪不怪了。如此若用美国的标准来“普世”中国,中国显然还没有“达标”。事实上,中国整个来说治理得是不错的,中国没有按西方标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崛起,不按自己实际办事绝无出路。鞋的大小只有自己的脚来试。
在中国历史上占主流的认识论并不是什么“普世”,而是经世的学说。经世致用一直是中国主流知识分子追求的境界。中国“四书五经”主张得更多的是经世而非“普世”的观念。但也不能说中国没有遭受“普世”之害。比如宋朝,宋人讲的“天理”就是那时的“普世价值”,宋朝的知识分子很像今天满口“普世”的“公知”:宁可“灭人欲”,也要“存天理”。人欲是讲个性的,他们要灭掉,他们把女人的脚按一定的尺寸裹起来,这是真正的削足适履。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后来,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
人认识真理从而形成文化自觉,多在经历灾难之后。造成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宋明两朝败在北方游牧民族铁蹄之下的痛苦经验。宋朝的衰败刺激了中国人的文化革命,其革命的起点就是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为什么要求人们“正心”?“正心”就是讲个性,讲立场。“正心”然后才能有根,有根后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学问有了个性即立场的要求,只要你讲立场,就要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解决矛盾有时是要带刀子的。宋明两朝的灭亡造成的知识分子的大觉悟,其表现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大复兴。你看王阳明,他本人一边打仗一边治学;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个人都是大学问家,也都不放弃枪杆子。清朝的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藩就更不必说了。
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普世”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也要反对以西方为范本的教条主义。
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而是说我们不能以它们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绝对标准。王明曾将苏联经验绝对化,他们以苏联军事理论为标准,说毛泽东不会打仗;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带向湘江,出去时八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回来就剩下三万多人了。在血写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苏联教条的迷信,找到了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一些成功的经验甚至是毛泽东思想“普世”化、教条化。毛泽东与此进行了不懈斗争,1968年8月,毛泽东《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时,直接删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段落,并退回要求修改。9月26日毛泽东批评外交部接待计划中“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安排,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同时还删除了外交部拟定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9月29日,毛泽东审阅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时,删去第二页末段工宣队“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并明确批示:“这一句不要”。
关于此,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年12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记载。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对此有深刻的总结,他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已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也有些人开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们以西方为普世,以美国为绝对标准,似乎中国改革若不合美国的标准,就统统都不达标。这样的结果只能使中国的改革走向它的反面。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与“普世价值”、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成长的。党史前半部分多是跟“左”的“普世价值”斗争,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要与右的“普世价值”进行斗争。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的贡献就是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如果不这样,大家看看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的下场。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快要取得全国政权时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结果援助没到,自己却全军覆没。中国共产党走自己道路。1949年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不说鼓气的话,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
1942年3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后的经验教训,说:“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
在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们也要开展一场反对以“普世价值”为幌子的洋教条主义的启蒙运动。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弄清改革要依靠谁、为了谁,谁是我们的阶级基础?蒋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走不下去呢?他没有多数人的阶级基础,他的阶级基础就是中国的少数买办,买办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们表面上是坐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根部却是接通到美国的,这样的基础当然不牢靠。毛泽东将人民作为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这个国家就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符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在一次会上有同志说,美国还有发展的余地,因为它的技术潜力还在,其技术发明还有相当的空间。我说不对,资本发展的空间在于社会劳动可提供的剩余价值的多少,只有技术而没有剩余价值,资本家是不会采纳的。当今世界可为国际垄断资本提供的剩余价值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以至它们开始剥削到西方国家内部了,殖民地也开始向发达国家逆推,要不美国人民为什么要占领华尔街而不去占领白宫呢?这是一个重要现象,值得我们思考。
思考的核心还有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机械照搬他国经验问题。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前者是通往胜利的路,后者是通往失败的路。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资料来源:《党的文献》,2016年第4期)